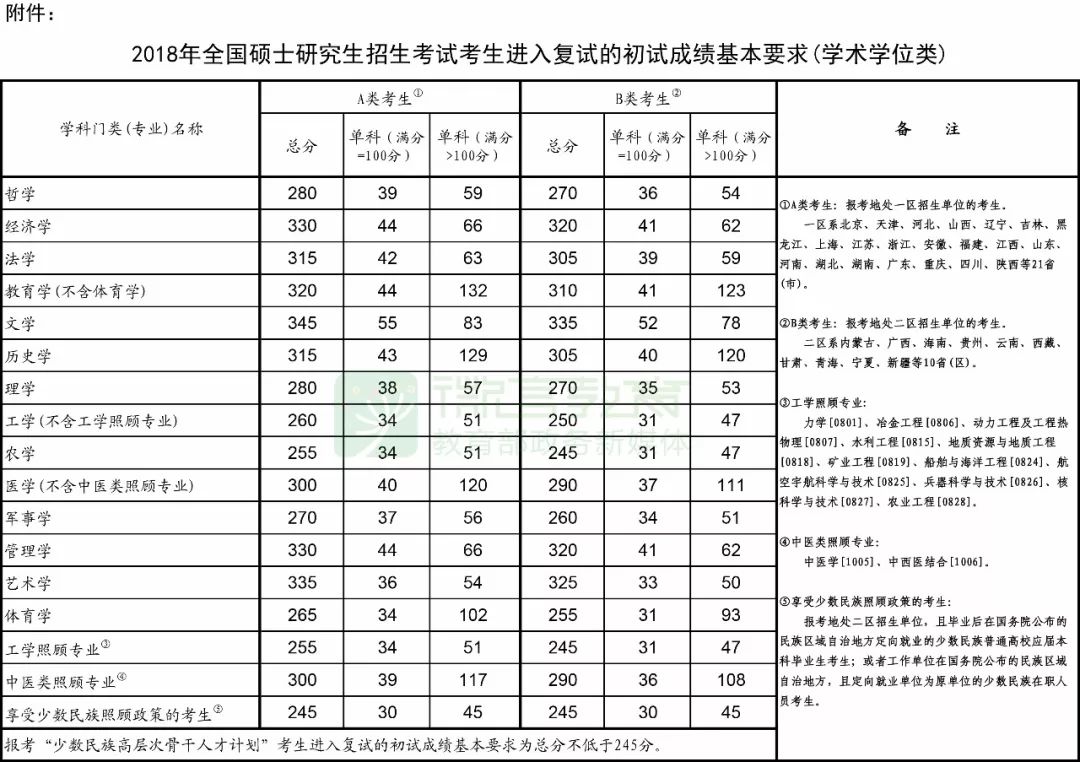学前教育的学者,在投影仪上展示研究成果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代表,在台前介绍最新的举措。公办和民办的幼儿园园长,一边讲述一边提问,表达各自的诉求。
2017年12月28日,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第二天,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,不同身份的人坐在同一个屋檐下,持续了一整天,进行了两次圆桌讨论,13个人上台作了报告。
主办方为财政部、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共同设立的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。该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解释,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,包括学前教育的办园体制、质量、监管和成本分担。其中,成本分担是教育部交给的政策研究任务,而监管和办园体制,是来自财政部的科研要求。这次会议“得到了两个部委的大力支持”。
“我们从10月份就在筹办这个会议,原本只是想邀请学者为主,进行单纯的学术型讨论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之后,我们就把主题改了。”宋映泉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,“想借这次机会,让不同身份的与会者,从不同的角度,对学前教育面临的成就、挑战、问题和对策进行讨论。”
入园难,入园贵,从业人员收入偏低,少部分从业者职业操守、专业伦理缺失,行政部门联动监管“缺位”……一条又一条的问题被罗列出来
作为北京民办幼儿园日日新学堂的创始人,王晓峰称自己为“家长办学者”。这个头衔,他更在意“家长”这两个字。最初的办学初衷,也是觉得“找不到满意的学校”。
前不久,日日新学堂所有的教学区域,都被主管部门要求装上了监控设备。但在王晓峰看来,这种“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方式”,实际上“效果很有限”。
“如何切实地避免我们的孩子受到伤害,这是一个难题,仅仅靠政府的监管,很难做到位。作为一位家长,作为一位家长办学者,我认为只有充分开放社会资源,发挥家长在幼儿园建设中的作用,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一问题。”王晓峰说。
他认为,比起肢体暴力,幼师的态度和情绪等冷暴力,对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更甚,“监控也无济于事”。
来自山西某地级市的一位普通家长,对此深有感触。她告诉记者,她的孩子5岁,在当地一所民办幼儿园就读。幼儿园老师会号召班里的孩子们,孤立疏远那些“上课调皮”的孩子,不理他们,不和他们玩。
她不认可这种做法,试着和老师沟通,但没什么效果。她直接去找了园长,情况才有所缓解。
“教育理念差太多了,我跑遍了市里的幼儿园,找不到满意的。”这位母亲在北京工作过,后来回到老家创业。然而孩子在幼儿园遇到的问题,让她动了回北京的念头。“起码,把孩子送过去,有更好的教育资源。”
她也解释了自己没选公办幼儿园的原因。前些年,当地的公办学校统一取消了学前班,民办幼儿园仍会在教学中加入原本属于学前班的课程。这导致公办园的孩子升小学时,比民办园的孩子少学了许多东西。
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张燕的报告中,取消学前班的行政指令,属于“过度的人为干预”,体现出一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、单一标准化的办园取向。
一条又一条的问题,在这个关于学前教育的论坛上被罗列出来,摆在台面上讨论。这些问题包括入园难,入园贵,从业人员收入偏低,少部分从业人员职业操守、专业伦理缺失,行政部门联动监管“缺位”或存在“盲区”,卫生保健人员配备不足等等。
这些问题密集而沉重,曾零零星星出现在网上的言论中,家长的口中,以及专家的研究报告中。
刚刚过去的2017年,中国的学前教育,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。上半年,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出台《学前教育法》。下半年,发生在幼儿园的种种虐童事件,从上海到北京,从大都市到中小城市,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讨论。“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”,出现在中共十九大后第一个全国性会议—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部署里。
金字塔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间,被低层次的民办幼儿园所占据
河南一所公办的省级示范幼儿园,每到招生阶段,网上排队报名的人数,便会飙到实际招生人数的成百上千倍。
“第一次实行网上招生的时候,几分钟就招满了。第二天,没摇到号的家长们把幼儿园的大门都堵了。”这家公办园园长感慨。
对于这种现象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佘宇的解释是,目前的教育财政投入,主要集中在城市或县镇公办园、机关园,尤其是优质示范园。
作为民办园园长,王晓峰也觉得,开放给公办幼儿园的教育资源太多了。他注意到,2011年,广东省政府8所机关公办园,获得了6863万元财政拨款,远超民办园的投入。很多公办幼儿园“每年都在发愁钱怎么花出去”,与此同时,大量的民办园捉襟见肘,“形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”。
这些资源不仅仅指财政资源,还包括教育培训等各式各样的资源。
“我认识一个公办幼儿园的朋友,他说他们的老师,都被教育部门培训得‘恶心’了。而我们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呢,想被培训都没有机会。”王晓峰感慨。
他觉得,民办园教师整体素养不足,或许也是“一些极端情况”出现的原因。
会议上展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,大量民办幼儿园,由于缺乏来自教育财政的成本分担,使得这些幼儿教师一边承担着繁重的工作量,一边拿着极低的工资。
甚至,一些基层的公办幼儿园都很难留住素质较高的老师。一位与会学者谈起自己调研经历时说,他发现许多农村的公办幼儿园,“校舍在,孩子在,老师没了”。
不止一位民办园园长在这次论坛上呼吁,开放更多的社会资源给民办幼儿园,比如财政投入,比如师资力量,比如对土地或房产的使用。
有些在一线城市办园的民办园长,好不容易把幼儿园办成了,房租却涨了,不得不重新寻找办园地点。
在中部某一个县,县政府以没有土地使用证为由,拆除了41所民办幼儿园,让不少办学者担心自身的处境。有学者推测,此举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当地公办园的占比和招生人数。
国家统计局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(2011-2020年)》统计监测报告显示,2016年,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学校24万所,其中,公办幼儿园仅有城市1.74万所,农村6.82万所。
无论是办园数量,还是在校幼儿人数,民办幼儿园占比都超过了一半。其中,大部分民办园,都是规模较小的地方性运营商。只有少部分民办学前教育机构,打造出了特有的品牌,形成教育集团并开始扩张。
如果将目前中国幼儿园的整体状况比喻成一座金字塔,立在塔尖的是高品质民办幼儿园,中间夹着一层公办幼儿园。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间,被低层次的民办幼儿园所占据。
2017年5月24日,中国的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开始实施,为期三年,目标是到2020年,“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%,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%左右”。
普惠性幼儿园这个概念,指的是公办幼儿园以及由政府出资补助并制定收费标准,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。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认为,大力发展具有公办性质的普惠性幼儿园,才是解决入园难、入园贵问题的方法。
她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,政府应当“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,新建一批面向大众、特别是优先招收社会中低收入家庭幼儿的普惠性幼儿园”。
政策是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成长,而不仅仅是为了管理
佘宇坐在台前,从入园问题到幼教人员问题,一条条地列出来,再一条条地谈自己的应对建议。“发挥政府主导作用,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直接提供公共服务。应当给民办机构、多样化需求留出空间。”
他认为,政府在学前教育中,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监管、托底保障和提供资源。而公办园和民办园哪个占主体,“或许不是关键所在”。
张燕在报告中提到,政府往往倾向于,给原本已经很优质的公办园增添更多硬件设施。与此同时,多元化、多样化的幼儿教育,却正在面临着生存困境,“民办教育受挤压,自办园遭取缔”。
在场的几位学者都认为,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,应当“雪中送炭”,而不是“锦上添花”。应当优先投向人力资源,保障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,最终才能促进质量的提升。
“公办园的生均办园成本,远高于民办园。政府财政在优质幼儿园中的成本分担比例高,而在普通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中的分担比例极低。这不利于促进学前教育的公平,也不利于学前教育发展的效益。”宋映泉指出,“政府的责任,是保障弱势群体进入有质量的幼儿园,而不是扩大不公平。”
冯晓霞同样也强调了“雪中送炭”。但她也认为,从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质来看,如今我国的民办园,在幼儿园总体结构中所占比例过高,这其实并不合理。
“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,让幼教行业迎来政策和人口红利。在投资机构眼里,幼儿园是‘现金奶牛’,是暴利的行业。当资本快速进入,形成巨大的幼教产业集群,其消极后果之一,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,‘虐童’事件频发。”她说。
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,学前教育机构主要包括教育部门办园、机关或事业单位办园、集体办园和私立园4种。带着公办性质的前三种占了幼儿园总数的90%。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,第二和第三种幼儿园被大量关停。
论坛结束后,夜幕已经降临,她与宋映泉仍坐在会议室门口的沙发上,继续讨论幼教话题。
“管理体制和办园体制逐步理顺,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进一步落实。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普遍建立,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。幼儿园教师配备和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初步建立,师资力量进一步加强。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监管体系基本形成,办园行为普遍规范,‘小学化’现象基本消除。”在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》中写着。
“仅仅有好的政策是不够的,能不能执行到位才是关键。”冯晓霞说。
“政策是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成长,而不仅仅是为了管理。”这是民办幼儿园园长王晓峰的期待。